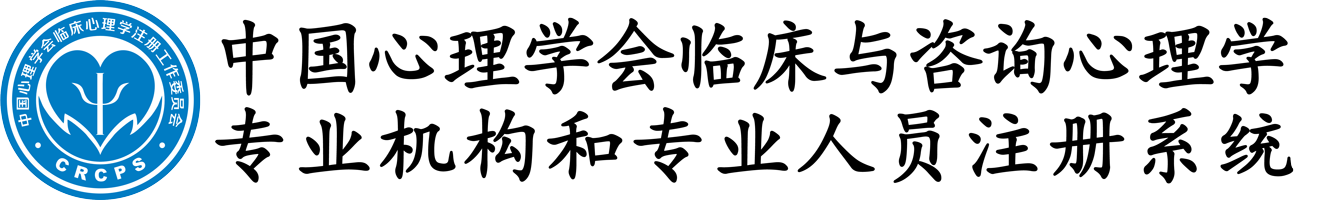赵旭东教授:像绣花一样看病
作者: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 时间:2015-05-08
他看上去有些疲惫,连续接诊五个病人,每个病人维持五十分钟。但倦意无法遮掩笑意,他的嘴角似乎总是向上弯着。专业术语夹杂着云南地方话,很复杂的事儿,他说着说着,就简单了。
“我的导师当初问我,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行?我说,这世界上,不开心的人太多了,我就是要做些事,让人觉得开心,觉得好玩。”一晃三十年,他不改初衷。经常对病人说的话也是:你来时愁眉苦脸,五十分钟过去,你现在满脸笑容,我很满足。
这位中国精神医学界的开拓者之一,选择这项职业时,偌大的医院里,甚至还没有精神科。他协助老师万文鹏先生,将首届中德班引入中国,因为这传播的功绩,荣获奥地利“弗洛依德奖”。
周涵:
您刚才说看了五个病人,医院里和咨询室有什么不一样吗?
赵旭东:
我是精神科的心理医生。看的范围非常广,从酒精中毒性脑病,到儿童恐学焦虑都有,有咨询有治疗,但多数可以下诊断。大半不在这儿开处方药,像今天的两个病人,就不需要吃药,坚持用心理治疗就可以了;有的人不想吃药,以为通过咨询就能好,但我会劝他必须吃药或住院治疗。
周涵:
这肯定要依凭一些治疗指征,在这方面,您有没有属于个人的经验分享?
赵旭东:
这需要非常丰富的精神病理知识的临床经验,如果没有,再严重的病例到跟前他也不知道,还在咨询,那就是胡来。但有的病人以为是灭顶之灾、不治之症,反而并不严重,只需要心理治疗就可以。
周涵:
但人们往往会觉得,到医院就得开药。我有个朋友失眠了,一到精神科就给他开安眠药,这会不会有其他综合医院里滥用抗生素的感觉?
赵旭东:
在这儿,我是50分钟一个病人。在国内,这是很奢侈的事情。我会问得很仔细,知道他大概处在哪个阶梯。很遗憾的是,国内医疗机构精神科大多没有这样的条件,可以预约病人。大多还是老的模式,来多少看多少,一天四、五十个,没有太多时间问病史,无法探讨到细致的内心体验和生活历程,也没办法全面判断人的人格特点、并发症及社会功能、关系等,当这些没法展开时,最简便的方式,就是使用药物。这种模式很多病人不喜欢,医生也不满意。
周涵:
这一现状是否在改善?
赵旭东:
一时半会改不了。医生在比赛看多少病人,这是荒谬的,精神科医生不应该多看病。在这儿,我是故意的,我要做给他们看:精神科医生,就是要像绣花一样看病,这是我的老师,华西医院的袁德基教授曾教导过的。我不习惯,也不安心3分钟看一个病人,我觉得这会伤害到他们。当然,有个补救办法,就是另外可以预约再做心理治疗。
周涵:
您经验丰富,病例复杂广泛。那么在临床上,您最常见到哪些病例,在您个人看来,导致这些病症的普遍因素是什么?和如今的文化背景、社会现状有什么样的关联?
赵旭东:
这得写部教科书了。遇到最多的,还是焦虑障碍,心境障碍。说到焦虑,大家都在议论,但并没加以分别。其实它有很多亚型。比如焦虑就有很多,社交、场所焦虑;还有疑病症、慢性疼痛、其它神经症性障碍。你问的第二个问题,总的原因是有很多种,主要有两大类。主观方面,大家认识疾病的态度、标准、求助方式和渠道都发生了改变。这些病症如焦虑、抑郁早就有,以前没当它是疾病,也没有觉得需要帮助。你就熬吧,熬不过就死吧,实在不行,就找组织去找妈去。现在有医生、有网络,求助方式改变了,好像一下子毛病就多了,其实咱们父辈不见得心理就健康,只是他们不呻吟不叫唤。第二个原因,是实实在在的。空气污染、有毒食品、水污染,这些会伤脑袋的,比如喝酒会喝成脑病。今天来的一位企业家,就是因为喝成脑病,他不爱讲话,对什么都不耐烦,没有一个医生问过他喝酒的情况。我受过两年当神经科住院医师的训练,知道这是器质性的,慢性酒精中毒。但不知道呢,就难下诊断了。当环境有害因素增加,压力增加,而且长期慢性持续存在,就会导致心身医学的问题。还有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,比如家庭独生子女结构,一个孩子也会增加父母的焦虑;社会老龄化,老年抑郁就增加了,这都是实在的。
周涵:
“我们上辈有毛病,只是不叫唤”,而我们如今动不动就喊“病”,号称“人人都有病”,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以接受的态度,而我们现在以对治的方式?到底哪种方式更有利于身心呢?
赵旭东:
在心理健康问题上,没有统一的科学标准。人类苦难有史以来就没少过,现在是以心理学、医学病理学的模式,以前是由宗教、哲学价值观来解说。不同的文化解说,直接影响了对待痛苦的态度和做法。有人求宗教解脱,有人吃药,有人跳大神……问题五花八门,方法五花八门,解释和总结标签也五花八门。现在总的趋势是先从临床得到警醒开始观察,再通过流行病学、变态心理学等提供数据,来知道问题有多严重,但基本形式没有改变。
周涵:
这种阐释,会否因为贴上“病”的标签而加重内心的不安甚至恐慌呢?
赵旭东:
从群体讲,不一定有恶性后果,提高认识有积极作用。但具体来说对那些精神科滥用标签诊断,使病人产生“标签效应”,从而是一些患者“慢性化”会有负作用。但整体来讲,重视心理卫生,从总体效果还是比较积极。反倒是你们媒体要注意,避免将心理疾病妖魔化,造成“人类疯狂”的心理错觉。
周涵:
焦虑有史以来就有,是因为最根本还是来自于“死亡”和“自由”的存在焦虑吗?
赵旭东:
这是个抽象的哲学问题,大家都在讨论。临床来看,焦虑的最急性表现如惊恐发作,其实来源就是最大的两个“怕”,也就是终极的怕:一个是怕死,一个是怕发疯——虽然他可能表现在怕心堵,怕脑袋中风——这是人类几百万年进化而来的,恐惧的基本情感模式,也是机体存在所必要的生理心理反应。
周涵:
如果单从现象,不从终极来说,比较普遍的是怕什么?
赵旭东:
广泛的焦虑,就是不知道自己怕什么,浮游性的,像热窝蚂蚁,感觉焦躁,是所谓“期待性焦虑”,等着麻烦什么时候降临。如果知道怕的对象,那就不是焦虑,而是恐惧——怕幽闭空间,怕坐地铁,怕坐电梯,怕坐飞机、怕黑……所有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怕的对象:怕鬼,怕毛毛虫,怕和人面对面会交流……
周涵:
如果长期和这些意识状态相交流,心理医生自身如何能不被传染到,不被干扰到?您有没有个人的见解?
赵旭东:
我发现很多咨询师没学过精神病学,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,心理咨询师必须知道变态心理学,如果不知道精神科医生干什么,就不会知道来访者干什么?不该他治的,他拿来治,这会比较麻烦。
周涵:
这现象普遍吗?
赵旭东:
非常普遍。而且很多咨询师还看不起精神科医生。以为考个证,就可以帮助别人排忧解难。补充一下前问题:心理卫生工作人员,从选择这个专业开始就要经常问自己:是否合适做这个?动机是什么?如果图好玩,一点不好玩。因为你遇到的,都是大家认为扭曲、痛苦、沉重、变态的事情;轻松吗?肯定不轻松,心理障碍有时要人命。所以要不停觉察自己的动机。
第二,要权衡、评估自己的个性特征、长处短处。比如中德班的培训,要求学员进行自我体检,自身有没有问题和毛病,因为有很多人从事这行,是带着麻烦来的。他们想自我解脱,有献身精神。这些动机无可厚非,但如果没有觉察,没有适当的修正和规范,这些动机太强大,就会让人崩溃。
第三,是你的专业水平。你必须能觉察到自己能趟多深的水,能游多远,评估自己的掌控力,知道病人和自己的界限在哪里,这样才能充分评估风险。
第四,要有兴趣,有热情。把它当成探索,当成创造性的劳动、分享的乐趣,这样一来,容易保持情绪上的积极、饱满。
第五,要有私人生活,不能当工作狂,生活、工作一定要分开。
周涵:
您这是分享了心理师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,非常好,相信也能给大家很多启发。能否结合您个人来具体谈谈呢?您是如何做到的呢?
赵旭东:
我十八岁时决定当精神科医生。听上去是偶然,其实是必然。大三时上哲学课,中间有两个小时的医学心理学,听后觉得有意思。后来就问哲学老师,他说中国还没有心理学,如果你想从事这行,应该当精神科医生。后来了解才吓了一跳,那时根本没人主动当精神科医生,认为很可怕。但我自己的助人动机很强,当时就想,其他科都发展不错,惟独这精神科,这么欠缺,但里面的病人肯定很需要帮助。——我喜欢干不时髦的事。毕业后医院里没有精神科,我选择了最接近的神经科。就这么几经周折,我才当上精神科医生的。告诉你这段经历,我说的就是动机。当时导师问我,你为什么要选精神科?我说:“文化大革命”人整人,大家都不高兴,我要做些让人高兴的事。现在我也经常对病人说,我非常高兴,你来时愁眉苦脸,50分钟后你笑着出去,我非常满足。
周涵:
五十分钟让人转痛为笑,很难唉,您是如何做到?
赵旭东:
心理治疗是一门基于科学的艺术。它不是匠人的活,不是喜剧演员的表演,也不是巫师的超自然仪式,它是综合利用病人带来的信息以及动力,让他发生积极的改变。它必须因人而异。看每一个病人,都是投其所好,投桃报李,使用个别化的原则,量体载衣。
周涵:
能分享一下这项“艺术”吗?
赵旭东:
就拿我今天的个案来说。有最老的干部和最小的学生。老干部工作认真、严肃,责任感强。从没玩过一次扑克,打过一次麻将。每次看到弟弟打麻将,就会批评他玩物丧志。虽然如今老了,但工作劲头还像年轻时一样拼命。这样的人,往往“病来如山倒”。一病了就觉得完了,无法为国为民尽力了,这个社会要垮掉了。这样的人,要帮助他,就是让他好玩起来——我喜欢讲好玩。让他松驰下来,让他对儿女情长、靡靡之音、享乐主义……多少不那么反感,让他慢慢适当地接受。有时我就会针对他的严肃开玩笑。他睡觉睡不着,我让他用些好玩的方法:睁着眼睛,眼珠朝上看床头这面墙,不准自己睡觉,眼皮不准闭下来、舌头不能掉下来;心里念叨:“老子就要看看,跟本能做对,到底是什么滋味;看你能不能做到3分钟不闭眼!”这些就很好玩。在他的概念里,医生是不能讲粗话、脏话的,可是……当然,我和他已经很熟了,开这种严肃的玩笑已经有了较好的关系基础。还有这个小孩子,生于国际化家庭,成绩优良,除了汉语,还精通韩、日、英三门外语,却很不开心。到了医院里,遇到过的医生老还是讲不开心的事,所以来这里开始是很抵触的。我就和她讲学校里好玩的事,开玩笑、做游戏,让她画画……慢慢她就知道,她可以和以前不一样。这是用小孩子的方式放松地打交道。这些做起来要像行云流水,毫不刻板。
周涵:
听您描述我也感觉到好轻松,似乎也没有什么章法!
赵旭东:
开始时还是要学习章法的。1.1,1.12.,2.1之类,看了那么多患者、咨询顾客以后,就会非常灵活运用,让诊断治疗的流程非常轻松,轻车熟路。这有一个过程,大家都是从菜鸟开始。
周涵:
您曾在德国学过习过3年,体会最深刻的是?
赵旭东:
最深刻是个人成长方面。明白了自我的概念,有了自我分化与自我意识。阶级社会是有等级的,但程度不一样,僵化的程度不一样。中国人生活在高情境文化中,太在意别人如何定义自己,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意义,互相卷入,互相操控,影响非常大。这是文化上的制约。在这方面,我的印象很深。在国内,即使我们有机会自由,往往也不知道如何去享受这个自由。
这在学者、治疗师中,会表现为缺乏主动性、创造力,缺乏责任意识。不像在西方,强调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。所处理的病人,也都涉及到个人与家庭、单位环境如何协调的事情,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会很麻烦。
比如女儿36岁没结婚,如果是说教,就会教孩子要听爸妈的话,人家老人不容易……会逼一个苦恼的人接纳传统对她的影响;如果你有自主意识,就会教他父母,这不是你的事,是她自己的事,不要还把她当孩子。上次婚姻失败,就是你们干涉造成的,你怎么还要做这种傻事?如果按照传统,你会将他们限定在这种粘着中,无法成长;如果你完全用西方的,女儿像你说的那样自主,但如果处理不好,父母痛苦,女儿也会内疚。所以个性化、平等、自主这些概念,用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,会有非常微妙的操作在里面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要意识到什么是追求、什么是枷锁。
周涵:
不知道您是如何“微妙”地操作的?
赵旭东:
这其实是东西方的平衡,是传统和现代、甚至后现代之间的平衡。治疗师要学会怎么样利用家庭里积极的力量,来减弱、消除对个人发展的不利因素。
比如刚才那个女儿,如果你劝她,你从了你爹妈吧,或者告诉你爹妈,这不关你的事!——这都有很大风险,都涉及到个体和家庭,个体和群体,传统和现代的问题。爸妈还生活在五、六十年代的价值观里,要教育21世纪的女儿听老一套是不行的,但对老年人来说,女儿永远是孩子,要他们接受现实也非常残酷。这其间,就要艺术性地制造一个台阶,不能批评或是剥夺——否则他马上感觉你挑拨离间——要有一个火候,循序渐进,最重要的是方向:你把这个家庭带往哪里去。如果感觉到这个目标达到双方有利,他们就会合作。如果你问父母,你期望女儿的幸福是什么样?如果她要达到这种境界,多做什么事可以有利于她这样?……他们就会选择,这就变成他们自己的选择,用提问的方式让他思考,产生自己的答案。这样就皆大欢喜,促成“有关联的个性化”,你让他们都成长。我经常做这个手势(大拇指连接向下),中国的家庭,几乎从不把自己的配偶作为第一位。他们依然首先将爱继续首先献给老人,这两口子就好不长,也好不深。有小孩子了,又将精力放在孩子身上,两人又离开了。如果夫妻主轴不是最强大的,对上不可能孝,对下不可能养好自己的孩子。老年人转不过这个弯来,结婚后还要子女把自己当最重要的人,这就有麻烦,很多人摆不顺配偶的问题,以后这工作就很难做。
周涵:
但听下来,感觉您都是主动选择,比如当初进精神科。您的自主意识很强,怎么会对这个印象深刻?
赵旭东:
以前是不自觉的,只知道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到了德国,有个参照才知道,原来我一直在干这个事。现在人家如果说我过得不好,我就知道那是他们所定义的;但如果没有这种觉悟,就会真的觉得不好,会受他们的标准影响。不管好不好,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所谓自由就是这样:自由做决定,享受它带来的喜悦,也会接受意料到的或意料外的苦难折磨,这才是自由,是更好的处理自己的边界,而非任性妄为。
周涵:
您在德国学的是家庭系统治疗,但大家说起来,觉得您是精神动力学大师,您还获得过“弗洛伊德奖”?
赵旭东:
那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建树,而是因为传播的影响,是对心理治疗的几个流派——行为治疗、家庭治疗、精神动力学……进行传播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,不是单一的成果。第一期的中德班,是我和老师一起从德方引进的。第一批学员,如今有的喜欢被人称作“大师”,也陶醉于当“大师”,我很反感。如果谁自封“大师”,那么离亡灵也就不远了。
周涵:
从您主动选择的经历,感觉到您的特立独行,具有开拓性。但您又强调,对病人要像绣花一样,有细致性,这其间是否有什么矛盾?
赵旭东:
你问的这个问题蛮有意思。特立独行的人,常会和刚愎自用、冥顽不化、偏执联系起来。但其实特立独行,如果是真的有智慧,恰恰是跟环境要很好的一致。也就是换了一个角度,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再则,从事助人工作,一定要有专业性,需要精致准确,做到有根有据,这些素质和态度是必须强调的。所以我不会拍胸脯去担保什么。反倒越做越觉得如履薄冰,会用一种认真谦逊、谨慎的态度,和病人打交道,不会摆架子,拿腔调。
周涵:
您一直强调医生,强调科学性。这是否会意味着,很容易看见“病”,而不见“人”?
赵旭东:
我坚持做到特立独行,就是让病人在这地方,感觉到自己是人,而不是病人。让他们能感觉到我的尊重,感觉到我想听他们说,他们说的,我懂。这也就是心理治疗很强调的同理心,或者“共情”的能力。在见病人前,你不知道接下来的50分钟,他会讲什么。但他的故事再离奇,都不会超过人性。当他感觉到你在帮助他时,他不会觉得你冷漠,他反而会信任你。
周涵:
最后,业余时间您如何放松自己?
赵旭东:
看书、听音乐、旅行、有时会唱歌、跳舞。对我来说,跟家人、同学、朋友的相处是最最重要的充电。定期不定期出国旅行一趟,也会很有收获。国外我最喜欢的地方,还是德国。
国内毕业于昆明医学院(现昆明医科大学)、华西医科大学,先后获学士、硕士学位;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,获博士学位。主治神经症、心身疾病、心境障碍,如:失眠,抑郁、焦虑、恐惧、疑病,性障碍;其它神经精神科疾病;家庭、婚姻、管理心理问题。现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咨询专委会主任委员、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;曾受聘为香港理工大学名誉教授,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客座教授、日本立命馆大学客座教授,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中方名誉主席。荣誉: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奥地利“弗洛伊德奖”获得者。